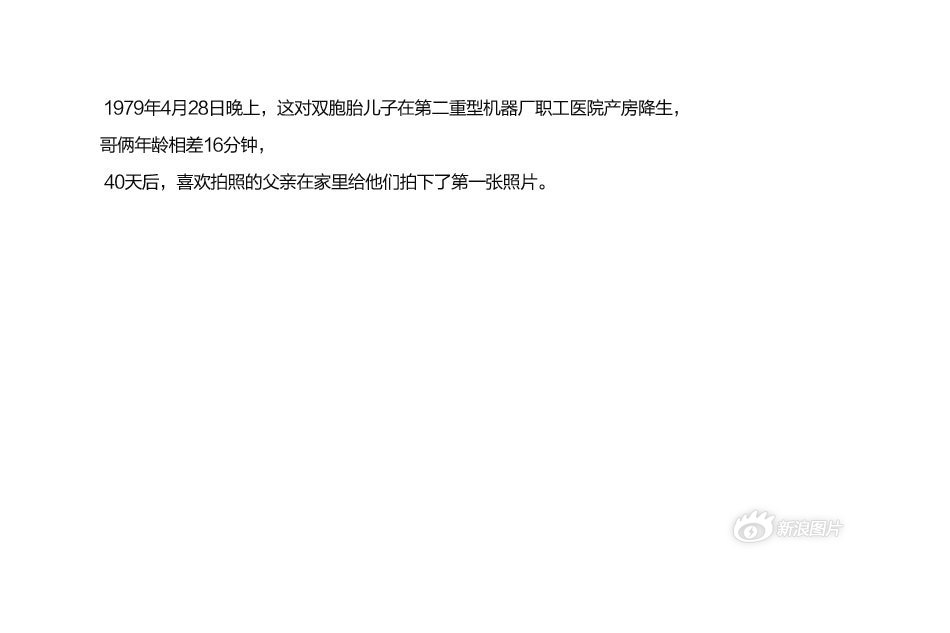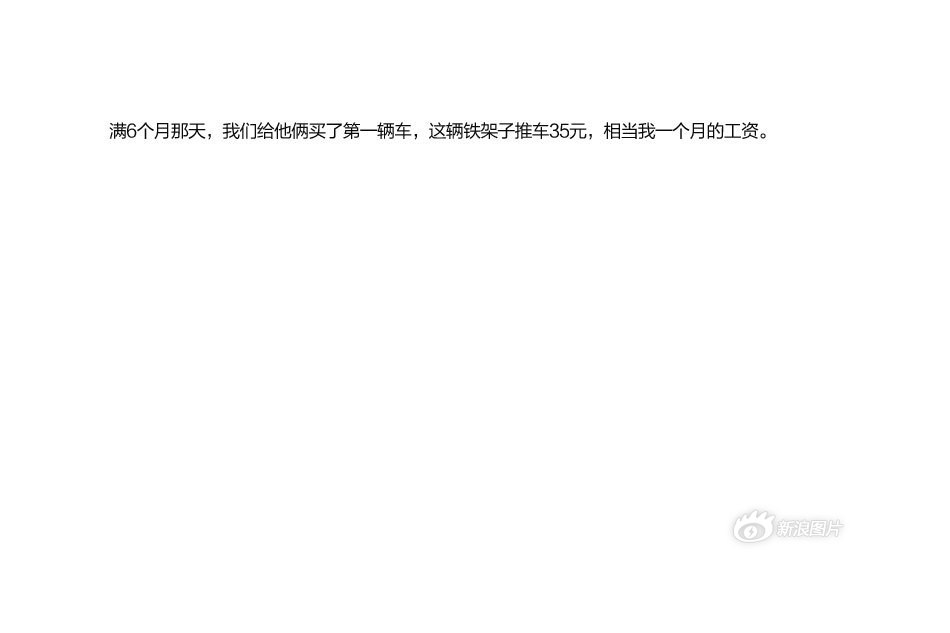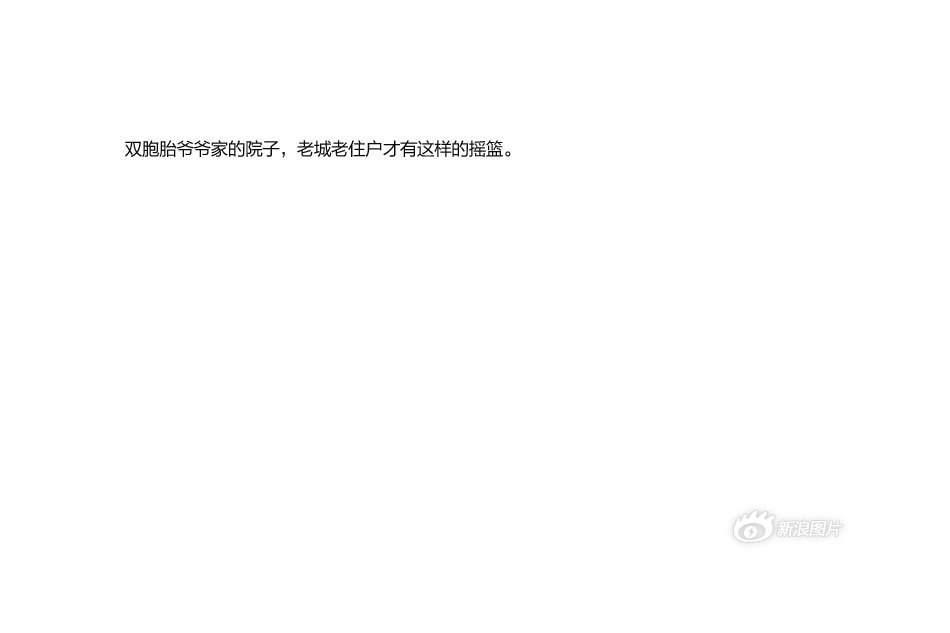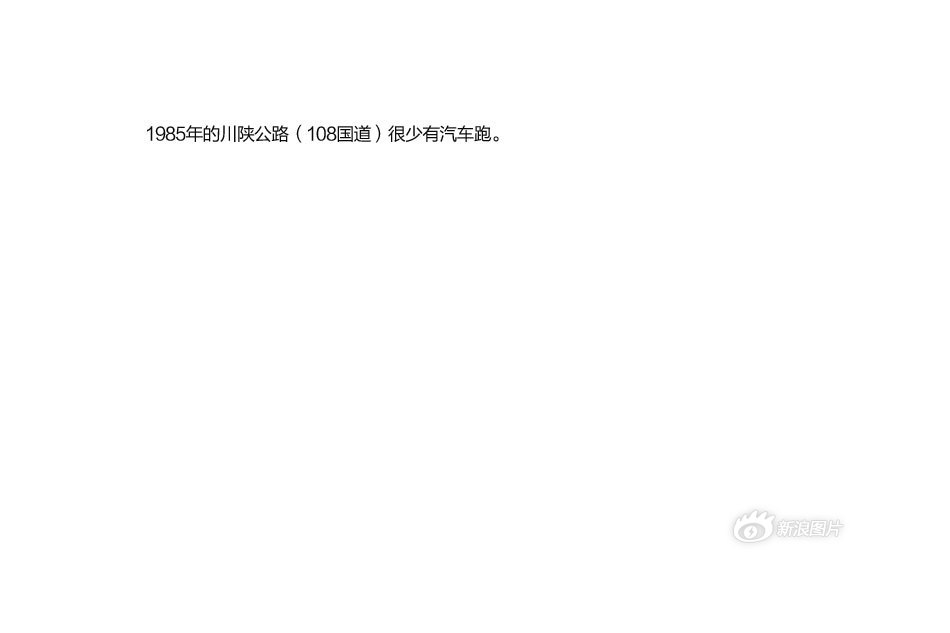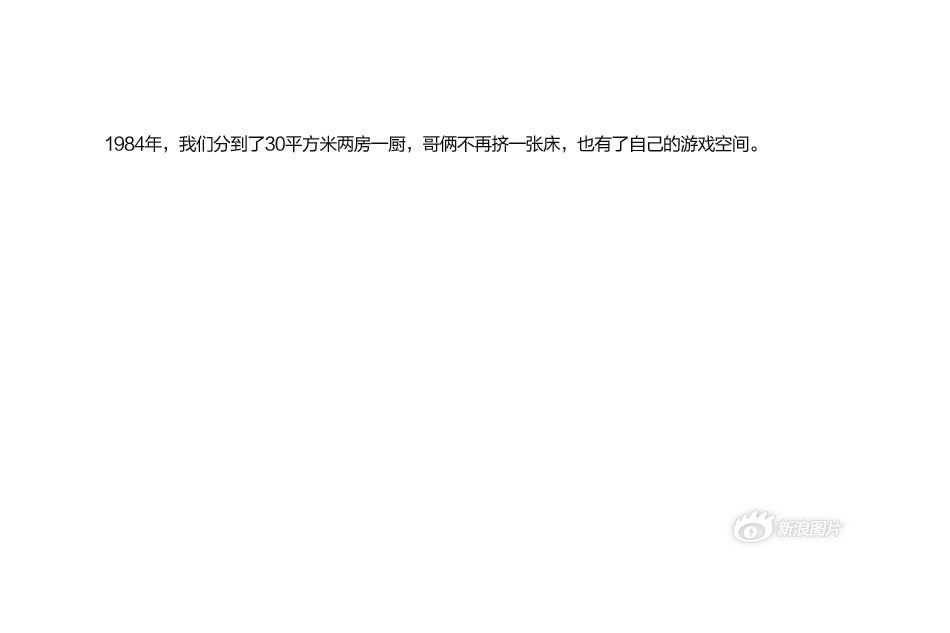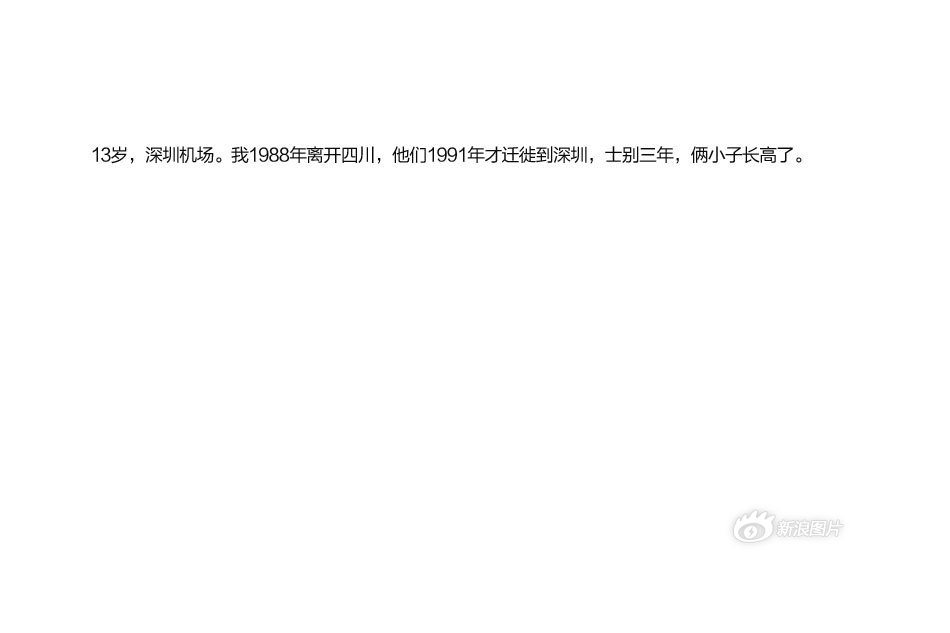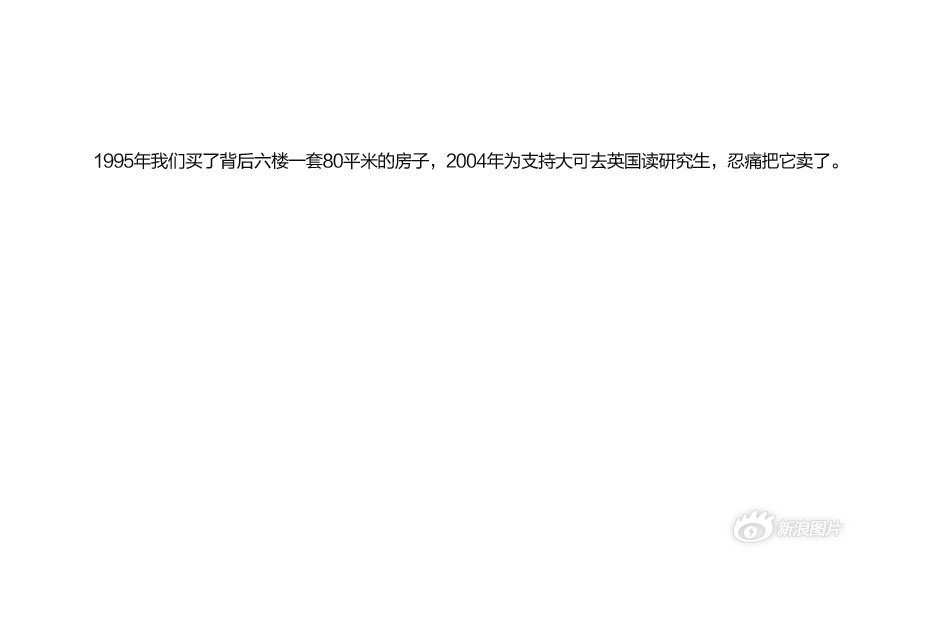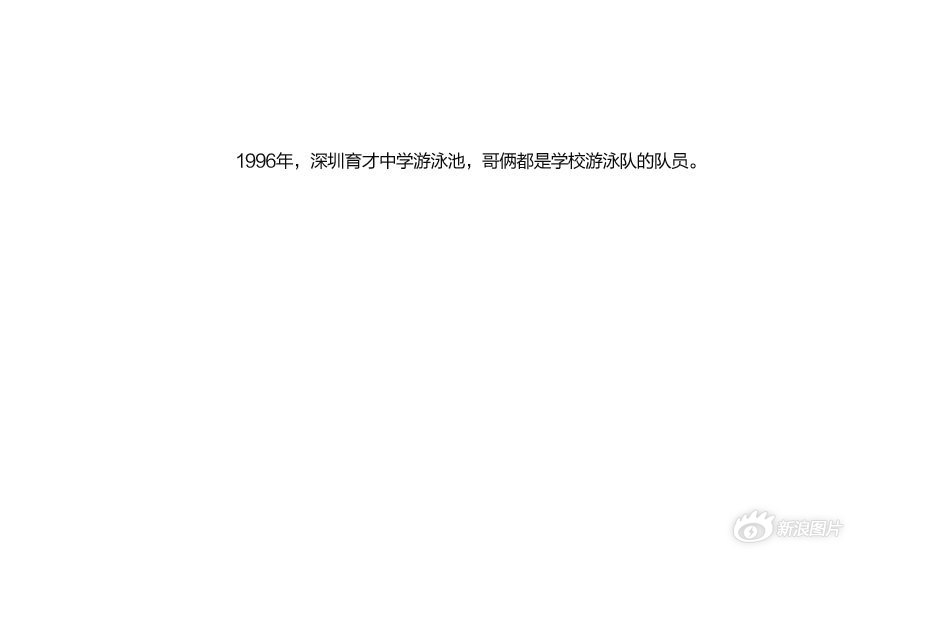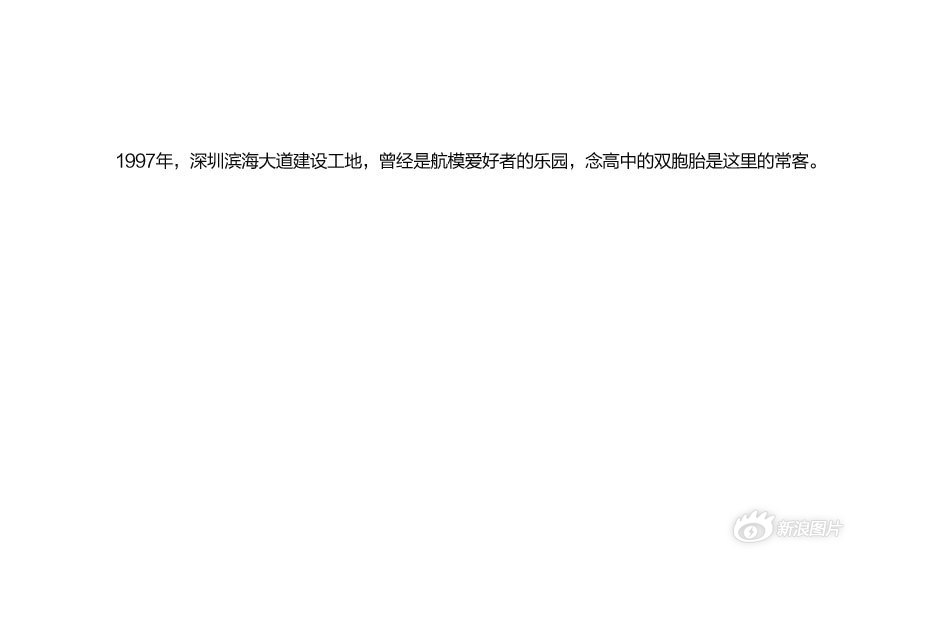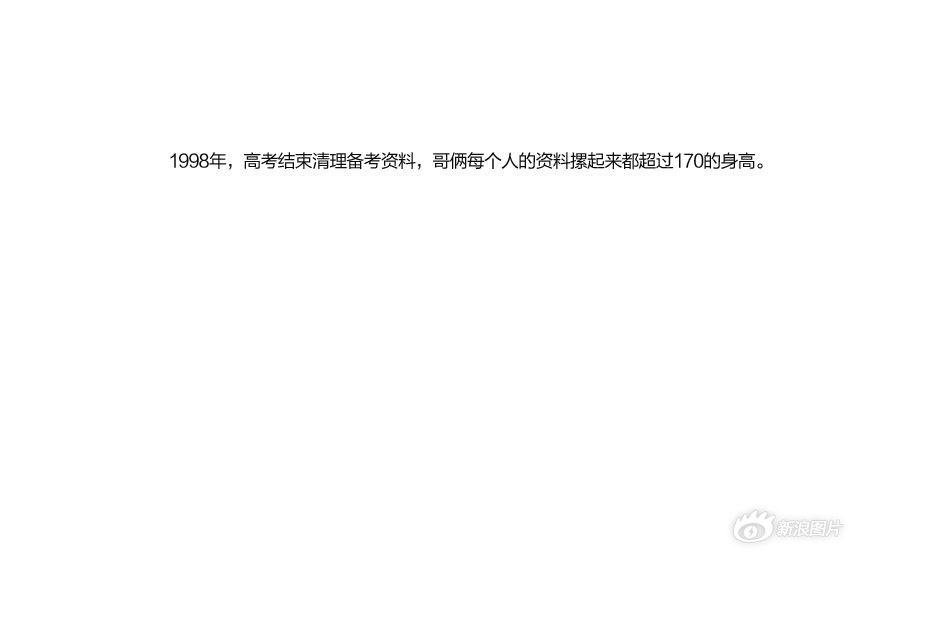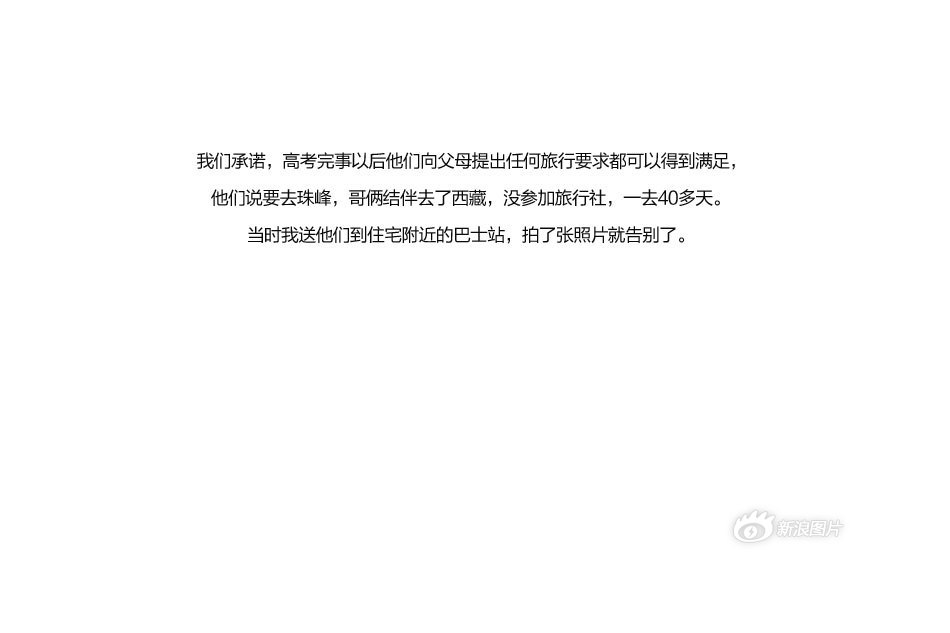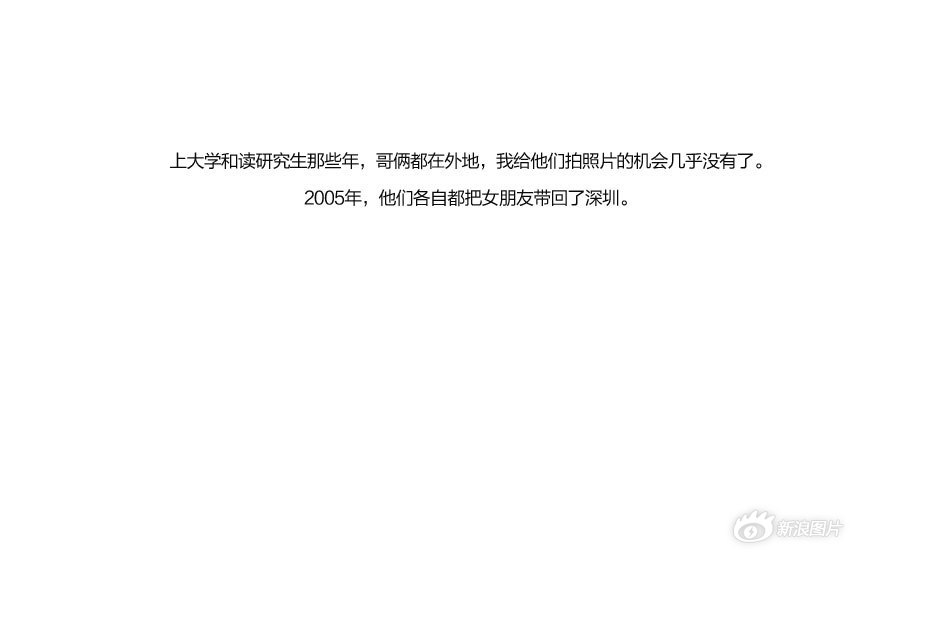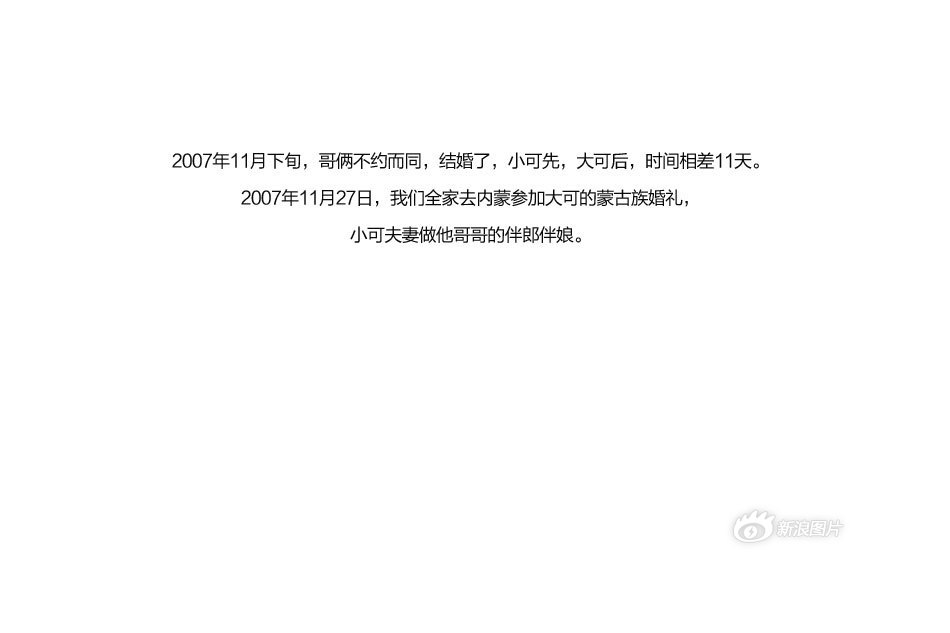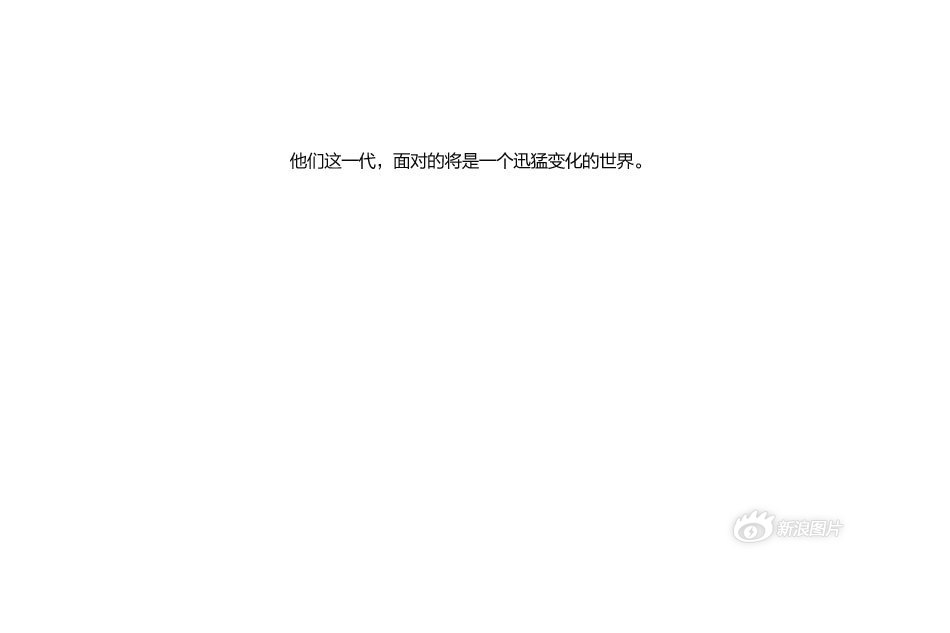文|张新民
1978年,我和妻子被派往山东潍坊柴油机厂(也就是现在的潍柴动力)安装锅炉,成天白菜萝卜皮儿,再有就是大葱沾虾酱咽着炝面馒头,妻子居然“有了”。那时候刚结婚一年,工资每月就32块钱,加每天3毛钱的异地施工津贴,俩人挣俩人花都紧巴巴,假如再来一小人儿,真就不敢往下想。可偏偏就有了,咋办?不要吧,一是下不了那狠心打掉,二也害怕两家老人们揪心,只好眼睁睁看着大肚皮鼓起来,直到干完活回四川。过完年,小人儿真来了,一来还俩,一前一后相隔16分钟,老大5斤3两,老二4斤6两,比起正常孩子,看着真是弱小,可还是让两家的老人们喜出望外。
那年头,个人穷,公家也穷。你即便有钱也买不到啥东西,更别说没钱了。我瞅着他俩,心想你们咋就那么着急赶着出来受罪呢?那就跟着大伙儿享受磨难吧。于是便起名“砥砺”——磨刀石,老大砥可,老二砺可。成年以后他们还一个劲儿抱怨我,说就我把名字给起坏了,让他们很不顺。
后来他俩的境遇果然艰辛。单位每月十号以后发工资,我们常常七、八号就只剩几毛买菜的钱了。更糟糕的是,妻子生产一年以后去读电大,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,晚上一点以后还捞不着睡,手上永远是洗不完的大盆大盆的尿布和小衣衫。1981年以后时兴超产奖金了,工人多干就可以多得20多元,而我偏偏在这个时候被调到上面去办一份小报,只能拿平均奖七、八元,比一线工人少很多。日子愈过愈难,我想,三十而立三十而立,连个家都养不起,还立什么立?
恰恰在这个时候,我迷上了拍照片。
迷上照片以后我就更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了。手上有点儿钱就挪去买胶卷,逮着一点空儿就往外跑,把他俩全扔给了妻子。1988年海南建省,新创刊的经济报愿意接纳我做摄影记者。妻子那年正在广州为一个工程做会计活儿,孩子在四川上三年级,我把我老母亲接来照看他俩的起居,铁了心要离开四川的单位奔海南。临走前一天晚上,老二开始发烧,但我已经买好了飞广州的机票,早上天蒙蒙亮,我摸摸他的头,发烫!我心里七上八下,箭已经在弦上了,不得不发,只好叮嘱我母亲,一上班赶紧带他去卫生院打针,然后一咬牙,走了。
到了广州已经黄昏,直奔妻子上班的地儿,她的同事很惊讶:你怎么还来这里?你妻子买不着机票,已经去了火车站,上午四川就来了电报啊你不知道?第一封电报说孩子病重入院,第二封电报说情况不好转院,第三封电报是病危通知!
天旋地转!我整个坍塌了。那一瞬间我仿佛看见了最坏的后果。我哪是父亲,是罪人。为了啥?是为了照片吗?那一年,他俩9岁。
在海南,后来在深圳,我确实是在尽力地拍照片,1990年至2000年拍摄了《包围城市——中国农民向城市的远征》 。农民们背井离乡抛家弃子到沿海发达城市谋生,看看他们,想想自己,本质上没啥区别。拍摄他们,根源在于我对农民们不顾一切也要改变命运的体验,我拍摄的,其实是自己的故事。
有关他俩的这些私家相片,多拍摄于幼年。如今,他们已经长大、成家,各自忙着自己的一摊子事儿,不大用我们操心了。空闲的时候会偶尔地翻一翻这些照片,看着看着,就觉得,自己老了。
栏目编辑|马俊岩
(声明: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新浪网立场。)